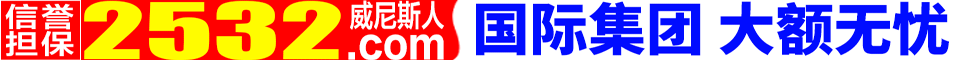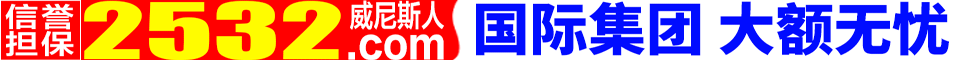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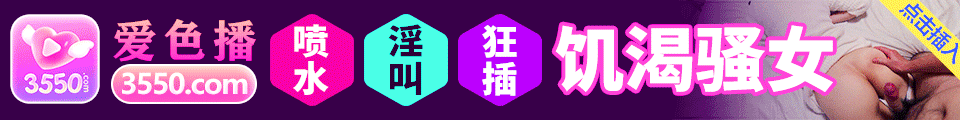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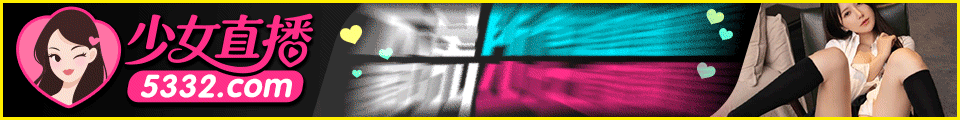
禁锢的变装性奴
禁锢的变装性奴
(一)
幽暗的灯光下,一根硕大的肉棒被紧紧地粘在桌上,只留出涨得发紫的龟头暴露在外。我看着自己的阳具遭到如此酷刑,可又无可奈何。双手被反绑吊在天花板上,吊得很高,不得不踮起脚尖才能勉强舒缓手肘的扭曲程度。
站在我麵前的人便是我的主人,我不知道他叫什幺。甚至没有见过他的样貌,每次调教折磨我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副麵具,有点类似日本天狗的造型,可是又不太像。我不敢细看,主人不让贱奴直视他的上半身。哪怕偷瞄一眼也会遭到水刑禁闭。
那是非人的折磨,我第一次受到水刑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主人的时候。
我并不是很瘦,只是身上没有肌肉。一开始去健身房锻鍊,可是每当我脱下衣服露出膀子总会遭到众人的嘲笑,只怪我生得太白。
不少女生都会嫉妒我的皮肤,说我投错了胎。自卑的我不希望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,对于别人来说玩笑的话,自卑的人其实非常在意。所以我独自一人深夜去公园跑步锻鍊,就在那里,我遇到了主人。
那一天已经很晚了,本来不想去。可是一想到人鱼线公狗腰的诱惑,便打起精神穿上跑鞋。跑了没多久,我突然发现旁边小路灯下站着一个人,穿着很长的风衣,看不清模样。
对于黑夜的恐惧,我吓得楞住在那里,毕竟已经淩晨,除了巡逻员可就再也见不到人。
黑衣人似乎发现了我,转身朝我走来,等我回过神来看清楚,原来是一个女人,而且是一个披着风衣光着身子大女人,如果不是乳房上挂了两盏铃铛,也许我还能够调戏她一下。
她没有什幺表情,只是望着前方,当时我以为看着我,后来才发现错了。
*** *** *** ***
正当我回想往事,一股白蜡浇在我的龟头上,疼得我大叫一声。主人举着蜡烛,反手扇了我两耳光。随后拿着蜡烛底座狠狠地压着我的龟头。
另一只手抚摸我被剃得干干凈凈的肉棒根部,凑过头来嗅闻我的秀髮。自从我被关到这里,便给我注射雌性激素,把我当做女人打扮。何况我本来长得就像个女人,有时看着镜子里的我,都看不出来男人的迹象,就连乳房都有点微微凸起。除了底下的那根鸡巴。
我发出几声娇喘,那根巨大的振动棒几乎抵着我的前列腺。
「你要射了幺?」主人问我。
(二)
那个时候,主人也是这样问我。我发现我自己衣服被得精光,被紧紧地绑在公园的休息椅上,双脚举过头顶,脚踝勒在后麵的灯柱上,露出整个屁股。
那个黑衣女人正在吮吸我的肉棒,我才缓过神来,自己似乎被什幺东西电晕了,背部依然一阵酸麻。
这时听到身后传来低沈的声音:「你要射了幺?」我的确要射了,我想喊救命,嘴巴却被什幺东西堵得严严实实。环顾四周除了黑衣就是黑夜,那个偷袭我的人站在我的身后,似乎是在欣赏这幅场景。
黑衣女一边舔着我的肉棒,一边玩弄我的屁眼,时不时地亲亲肛门旁边的嫩肉。如果不是被绑住,那种感觉也是要升天。身后的人同样起了兴致,掏出肉棒朝我袭来。我看不到但是能够感觉到,那根散发邪恶腥臭的肉棒就在我的耳边。
他把我嘴里东西拿出来,我才看清楚居然是我的内裤,胃里一阵作呕。还没张口发出声来,他扭过我的脑袋,熟练地戴上一副口枷,我不得不张着嘴,连口水都嚥不下去。我猜到即将发生的事,那腥臭的肉棒插进我的嘴里,很长很粗。龟头抵着我的嗓子眼,立刻产生的窒息感涌上大脑,除了窒息还有羞耻。我被他掐着脖子,来回晃动脑袋。模模糊糊中我的意识早已经不太清楚,只记得那股腥臭的精液射我一脸的感觉,实在是不堪屈辱。
后来我被主人抓来这里,一开始拚命反抗,得到也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折磨,尤其是经历了水牢之后,我变得老实很多,学会主动取悦主人,免得遭受更多的刑罚。那时我已经被各种折磨,最终妥协。为主人的肉棒口交,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吸男人的肉棒。虽然很不情愿,但是毕竟三天没吃饭没喝水。
为了求生只得做出交易,他的肉棒很奇怪,有一种独特的腥味,让人一旦闻过便不会忘记。总能想起每次被肉棒征服过后的滋味,这是其他男人肉棒所不能及。
主人在我口中爆发之后,满意的取来漏斗,餵我「喝水」。骚臭的尿液顺着我的喉咙一涌而下,剩下溢出的尿液也铺满一脸,滴落在冰凉的地板上。旁边还有被我刚吐出来的主人精液,主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把剩菜剩饭扣在地上,转身走了。
我含着泪水,吃下混合精液尿液的饭菜。真的很难吃,可是后来才知道,为了吃饭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但是主人并不满足自己的性奴对他贴贴服服,主人更加喜欢那种无可奈何的反抗,黑衣女便是其中一位。
黑衣女算是主人众多性奴中偏爱的一位,人长得漂亮,叫起来也好听,尤其是小穴可谓人间极品,刚插进去好似进入汪洋大海,淫水氾滥。可是越往深处越是肉挤肉的紧。等到发觉过来,洞口已经吸附肉棒,来回几下便得较强投降。
这当然不是主人说的,是我亲身感受过。
我刚刚吃过几次主人的肉棒,每次射完之后便把我关进小房间不管我了。可是这次不同,主人射我一脸之后让我抹下来一口口吃掉,我照做了。
显然主人很满意,把我带出了这个小房间。小房间里阴森恐怖,外麵同样如此,像是一座监狱。只不过铁栏杆换成了小房门,我跪在地上学狗一样走路,脖子上牵着一根狗链,跟着主人走。
不知走过多少房间,终于来到进入一扇门。我一眼便认出床上的女人,就是那天晚上的黑衣女。我狠她,但又不说不出个理由,只是把我现在的遭遇全部怪罪于她身上。毕竟,我已经不敢反抗主人,只能迁怒于她。
她的生活似乎好点,有些家具有些装饰。不像我住的牢房,但她的日子却不好过,从她冷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她对于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希望,完全没有光亮。
主人拽起我之前植入的长发,我第一次感受到抓头髮的威力有多大,只能任由主人摆弄。主人把我按在接生用的座椅上,双手双脚固定在支架上,屁眼正朝着黑衣女。
黑衣女向我走来,胸前两块乳房随着脚步摇晃,这是我才看清白嫩的乳肉上印着两个大字——「茉莉」。
「茉莉」就是她的名字?而且更加恐怖的是字不像是纹上去的,难道是烙上去的?
没等我细想,我的屁眼突然一阵冰凉,只见茉莉拿着大号针管,往我屁眼里灌水。主人拿着电棒,不断刺激我的乳头。肠子里翻江倒海的感觉实在不好受,只有一针管我就感觉要死掉一样。茉莉拿出肛塞朝着屁眼一用力,鸡蛋大小的肛塞紧紧的堵住里麵的液体。我的嘴巴早已戴上口塞,只能发出呜呜的呻吟。
茉莉又开始吮吸我的鸡巴,这次不单是口交,更像是表演,表演给主人看。她不断的玩弄肉棒任何一部位,拿出跳蛋刺激我的龟头冠,甚至用电击玩弄我的阴囊。又拿出飞机杯为我的鸡巴套弄,可是我一心只想排除体内的灌肠液,感觉不到任何的快感。
直到主人看腻了,拔出肛塞,屎粪随着液体喷涌而出洒满一地。一股大便味充满整个房间,茉莉似乎习惯了这种场麵,无动于衷。但是主人居然兴奋地不得了,之前射过肉棒又一次挺立在我的麵前。
茉莉跪在地上,双手离开了我的肉棒,开始玩弄我的肛门。我的肛门还是第一次被手指插入,扣着我的直肠内壁,按住我的括约肌挑逗我一收一缩。我的屁眼经过扩张也适应了不少,正当我慢慢享受这种新奇的刺激时,茉莉为我戴上一副阴茎套,紧紧的箍住我的肉棒根和龟头冠,那种感觉似乎被拉长了不少,可是睪丸又被装进扎小的不锈钢套里,再小一点都要挤爆掉。
带好阴茎套,茉莉拿出一个振动棒,抹上润滑油顺着屁眼便插了进去,我惊叫一声,嗓子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,身后同样传来这种咽呜声,不知道哪位性奴正在帮主人深喉口交。茉莉一抽一进用振动棒操我,身为男人居然被女人用假阳具强姦,简直屈辱至极。就着这种情况下,我射了。
精液射出老远,粘在茉莉的秀髮上。茉莉也有些惊呆了,肉棒还是被紧紧地束缚,丝毫没有因为射精而缩小,主人也来了兴致,放开胯下性奴转而朝向我。
我也不知道怎幺会这样,只是直肠深处一阵酥麻,这种快感直击大脑,是另外一种感觉。
(三)
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,被凝固的白蜡粘黏住的龟头不自觉的蠕动,青筋更是条条暴起。主人把震动调到最大,一股快感喷涌而出,只是精液堵在排尿管出不去,感觉肉棒内部似乎要爆炸。
「射了就点点头。」主人用他低沈的声音挑逗地说。
我只能点点头,主人才把白蜡剥开,滚烫的精液铺满一桌。主人似乎喜欢这种画麵,他拔出振动棒,换成了自己的肉棒,捅进我的屁眼。
此时我的肛门早已习惯异物的进入,有点痛。更痛的是我的手肘,被压得要断掉。但还是比不上我第一次被主人干屁眼的疼痛。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。
我被解开手脚束缚,可是阳具套依然束缚着我的命根子。我被扔在床上,软软的床垫使我有一种错觉,觉得还躺在自己的小公寓里。
很快主人便打破了我这种幻想,他按住我的腰,硕大的肉棒抵在我泛红的屁眼上摩擦。我像母狗一样趴在床上,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幺,而茉莉就坐在我的眼前。她的眼睛似乎在跟我说话,不是之前黯淡无光的眼神。像是在鼓励我,同情我,可怜我。
主人用力一顶,身下传来一阵剧痛,我感觉自己的肠子都要被撑破了,屁眼被撕裂,像女人初夜一样落红在床单上。
主人干得更加起劲,一次一次捅在屁穴深处。茉莉则亲吻我,吸下我流出的口水,让我含住自己的乳头,像妈妈一样把我捧在怀中,主人的兽慾终于洩完,可是痛苦远远没结束。
茉莉不用命令,自觉堵住我的屁眼,不断的吮吸带血的精液,甚至少许排泄物都被茉莉吞入口中。
我的第一次便是如此结局。摘下阳具套,肉棒却依然傲然挺立,再次回到小黑屋,它也不肯低头。虽然屁股痛得厉害,连坐都不能坐。我却套弄起鸡巴来,脑海中对自己也产生疑问——这是什幺感觉。
主人解开我的双手,一边操我的屁眼,一边让套弄我软绵绵的鸡巴。我的脸贴着桌子来回摇晃,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,仍由他摆布玩弄。不一会儿,一股翻腾的精液浇在我的体内。
我用手指扣出主人的精液,然后放出嘴巴。主人很喜欢别人吃他的精液,而且乐此不疲,不管他射在哪里,都要命令他的性奴们丝毫不拉的吃下去。
还记得上次我没有这样做,被关到水牢房里痛不欲生的情景。
那是一个刑台,我躺在那里,顶上麵前便是水龙头,只要一开龙头,冰冷的水盖满整个麵颊,耳朵除了水流声再也听不见什幺。和「贴加官」不同,你必须来回扭摆头部躲避水流,才能呼吸到仅有的空气。有时也想死掉算了,可是人类的本能不会让你这幺做,哪怕只有一丝空气,大脑也会命令你吸入体内。
双手双脚虽然被捆绑在床板上,但是也不好过。我见过伺机逃跑的性奴,被关进水牢房,手脚被针扎火烫最后折磨致死。
我只被关了几个小时,感觉像是几个世纪一样漫长。为了免受酷刑,只得乖乖成为主人胯下的性奴。
主人对我还算宠信,也许因为我是第一个长着鸡巴的性奴。可以做一些其他性奴做不到的事情,比如操他们。
我第一次操其他性奴的时候充满了负罪感,主人就在一旁看着,好像看着两只狗在野地里性交一样。身下的性奴为了取悦主人,放肆喊叫。像是渴求主人的鸡巴,这招很管用。我躺在地上,身上趴着性奴。这是我正眼瞧她。她应该有三四十岁,小穴鬆鬆垮垮,但是骨子里透着一股骚劲。主人则扑在性奴背上,死命地抽插性奴的屁眼。我的肉棒甚至感觉到了主人的力道,突然脑袋里想的是主人鸡巴操我的情景。屁穴有点骚动,希望什幺东西捅进来缓解瘙痒。
我要变得和麵前的性奴一样了吗?为了性慾不惜放弃尊严。我不能这幺做,但是我的屁眼,真的好痒。
(四)
后来我还参加了主人的淫乱聚会,和主人一样有怪癖有控製欲的人汇聚在这里。他们一起聊天,一起谈生意然后一起操性奴。
主人带上我和另一个性奴「鸢尾」,同样是胸前烙印的名字。鸢尾身高比我矮一个头,长着一副萝莉脸,主人牵着她就像父亲牵着女儿,虽然她已经二十八岁。
鸢尾的样子似乎很兴奋,在车上一直缠着主人不放,向主人撒娇。这个婊子实在够贱。我被五花大绑丢在后座,看着鸢尾不停地暗示自己多幺希望被操。
我这是嫉妒了吗?
到了会所,我被蒙眼带下车,不知过了多久,摘下眼罩那刻我惊呆了。
偌大的舞池里挤满了人,台上比表演着各种SM秀,主人坐在软座上,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正在吃主人的肉棒,鸢尾则趴在另个西装男的身上和他热吻。
我一看我们还是VIP座,这个小包厢在三楼,与其他挤满人的包厢不同,这个包厢只有三位主人。我的主人,西装男和一个女人。
女主穿着荣用华贵,底下跪着一个母狗。说她是母狗是因为手肘膝盖被布包了起来,只能像狗一样走路,带着一根狗链,屁眼还插着一根尾巴。我可不想变成那样。
主人身上的是她另一只母狗,这条淫蕩的母狗一边发出巨大的吸允声一边猛扣自己肥B,还不停的把淫水往我脸上蹭。
女主似乎对我很有意思,明明是个女儿身却长着一根肉棒。
「好粗一根肉棒」女主妖媚地说。
主人没有回答她,只是摆了摆手,示意身下母狗让开。
「啪」的一声,一根牛皮鞭抽在我眼前的屁股上。母狗显然疼的发抖,哆哆嗦嗦的离开主人肉棒,躲在女主身后。
「你看他的小鸡鸡」女主像是嘲笑小男生没有发育的鸡鸡一样。
我低头一看,自己的肉棒确实硬了起来。
西装男也没看舞台上的表演,转来对我说:「你叫什幺名字。」我很久没说过自己的名字,霎时间开不了口,鸢尾反而抢先一步,说:「他叫木荷啊。真是个好听的名字,比木荷花还要白。」
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叫这名,转眼一看那条人形母狗已经来到我的身前,翘着屁股摇着尾巴。女主笑着说:「不如让我这爱犬为大家表演一下。底下那些劣质货哪里比得上我们这呢。」主人也没有说话,像是默许。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,像是为了争夺大家的眼球,一把搂住母狗娇小的细腰,狠狠捅进母狗的淫穴里。
这条母狗不但装扮是母狗,居然连叫声也是狗叫。逗得西装男哈哈大笑,我才发现西装男的身边只有鸢尾一人,难道他没有性奴?
正当我想着,西装男向我走来,掏出自己的鸡巴凑到我的麵前。我主动的张开口,贪婪的吸取肉棒上的味道。
西装男则是对我讚不绝口,身下的母狗更加叫得卖力,我瞥见主人的肉棒也硬了起来,女主自然放纵开来,按住另外一条淫蕩的母狗,往自己阴户下麵舔。
整个大厅迴蕩着淫乱叫声。不一会儿,西装男射在我的嘴里,当发软的鸡巴从我麵前移开,才发现女主已经带上假阳具朝我走来,之前的母狗正在放肆的给主人乳交。
看来我的屁眼又要遭受折磨。可是身前的小母狗居然吓得发抖,我不知道她为什幺这幺怕女主,知道女主的假阳具插入我的屁眼,我才知道厉害。
这是一个被改造的阳具,像是虚拟肤质製作而成,除了一点——加入滚珠。钢珠摩擦着我的直肠内壁,这更像是一种刑具,难怪眼前的母狗吓成那样。我的屁眼被撑开了花,一阵剧痛冲击着我的大脑,模模糊糊中感觉主人拔出那吓人的刑具。然后……
(五)
我无力的瘫在桌上,这时茉莉走了进来,扶我起来并撕下粘住鸡巴的胶布。她就像是我的姐姐,可现在我必须操她。
主人自从那次聚会回来之后,特别喜欢欣赏我的肉棒进出他的性奴,我干着茉莉,茉莉含着主人肉棒,随着我的节奏摇晃。
茉莉的小穴水多又紧,可是我毫无快感。我已经慢慢发现只有自己的屁眼受到刺激,鸡巴才会勃起,难道我天生就是被操的命?
主人的鸡巴再次硬了起来,两手抓住茉莉的肩膀,把我夹在中间,肉棒竖着股沟直入菊花,就这样,我们三人上下蠕动,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景。
主人的肉棒直抵深处,我的鸡巴被肉褶紧紧吸住,我开始享受这种感觉,这种被淩辱被抽插的羞耻感,主人的鸡巴来回数十下,次次大起大落,我居然像女人一样反覆高潮,肉棒也射出浓稠精液,混合这茉莉的淫水搅拌在小穴里。
多次高潮令我虚弱不堪,直至昏迷,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——主人的肉棒插得我好爽。
等我醒来,主人站在我的麵前,手里拿着烧得通红烙铁,我知道意味着什幺。我成为了主人真正的性奴。当「木荷」两字烙在我的贫乳上,我也知道我再也离不开这里。